放不下的思念——信的记忆□李春魁
天水晚报
作者:
新闻 时间:2025年05月13日 来源:天水晚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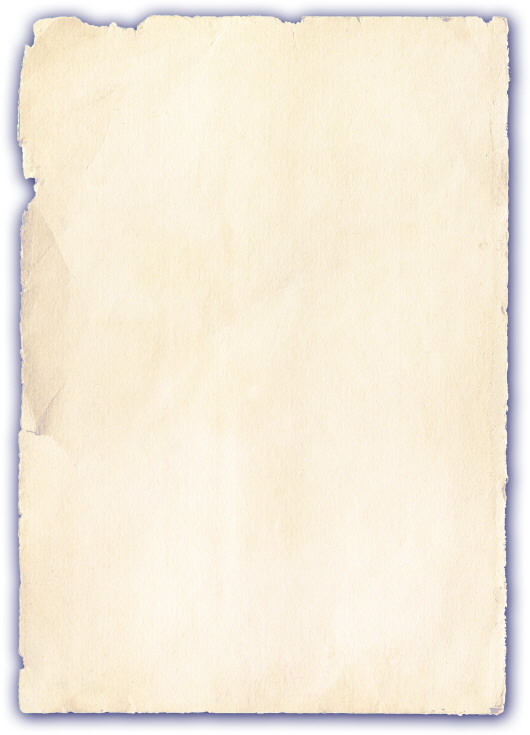
是无意中,是偶然间,从尘封已久的旧书信箱中翻出了几封纸已变色,字已变淡的旧有信件,抽出信笺一看使我激动,使我落泪,使我感慨,使我思绪万千……
1964年的深秋,父亲托二舅父写来的家信里,字字句句浸透着岁月的印记。信中絮叨着老宅门楣上被岁月侵蚀的砖雕;1965年奔赴新疆支援建设的大学同学张庚申的来信字里行间跃动着戈壁滩的炽热阳光,描绘着胡杨林的倔强身姿……
人,生活在世几十年或种田或做工,或读书或理事,不论做什么都要与人交往沟通,总要有人联系,在那科技不够发达的年代,尽管有多种形式交流,但信却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人人有亲情,有友情,有感情。人生每一个阶段每一段历程,从一封信中能让人了解一件事、几件事,几封信帮你解除一个疑难,一个问题,不乏实例。人,需要体贴关怀,需要温暖安慰,需要解疑启迪,尤其身在异域它乡。自己如此,外人如此,家人亲友无不如此。人生旅途情感是不能缺的,信件的阶段作用是重要的。
记得,1952年春季,我14岁读小学六年级,父让我给在河南老家的二伯父家写封信,我开头用河南土话称呼写的是二大爷、二大大,此开头后来堂兄指正说信开头应称呼二伯父母,这是我第一次写信。还是1952年夏季,自己从西安东羊市小学毕业独自乘车返回河南省延津县故里,因太想一块玩耍的孩子,就用不规整的字给家居西安市的魏宝丰同学写了一信,半月后收到他及他父母的回信,并要我们保持联系互通消息。虽然后因年久信失,脑中却留有很深记忆。
几十年的生活经历,我是盼望经常收到亲朋好友的书信的。那些时日,也就是上世纪下半叶,是很渴盼的:上中学等小学同学的信;上大学盼中学同学的信,刚工作或工作调动随时都盼望同学、同事、亲人的信。甚至暮年,同样盼着师长般关怀的张学忠同志的信。几十年前无手机,无电脑打个电话要去邮局排几小时队,一封家书也得十天半月天气,当然邮资长期是低廉的,信读过也是可回味的。
说起来不言庶民百姓,古代人、当代名人也重视书信。唐代玄宗时期的岑参《逢入京使》的绝句“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千百年前,骑马、口传、写信都是有的,通消息,报军情,报平安;还是唐代晚几十年的著名诗人张籍也写了一首《秋思》的绝句“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一封信也是可说很多事情的。
当代人,看重书信同样有太多的实证,曾国藩有家书传世;鲁迅《两地书》,不少青年从中受益;邹韬奋《读书信箱》为读者排忧解惑……古人也罢,名人也好,平民百姓的书信往来交流是经历、是经验往往让人身感同受从中汲取养分,哪怕点点滴滴、片片断断,只字片言。
遗憾的是大部分丢掉了存有个人经历的信件,现仅留的部分信件,其中有些牵扯家中私事,欲在闲暇时加以整理不知是否恰当和有益,思前想后尚存犹豫去信给钦敬的学忠同志,求释疑,他当即复函:“将一些通信编辑成册,一则是个纪念,二来引起无数美好回忆,确实很有意义。”这话是醍醐灌顶不仅给人以鼓舞,也加大了动手动笔之勇气,不妨一试,才费时日,下决心整理。
这些信,无论是亲人,是朋友,是同事,是领导,是下级,即使是一封素昧平生极平凡小人物的信,毕竟有些年份,时代不一样了。当时也许是“说不尽”“意万重”。这些可亲可敬可爱之人,有的业已作古,有的到了耄耋之年,有的虽尚在壮年甚或更年轻却“渐行渐远渐无书”因远离没有了消息。个人重读旧信,确实也显现各种感受,交织着错综复杂的心情,虽然身感同受,受过激励和启迪,可却不能预测多年后,后人翻看是何种感受,能否起到一些作用?
话又说回,“信”这个词,究竟指什么?当代辞书上说,信是“按照习惯的格式,把要说的话写下来,给指定的对象看的东西。”感到“东西”二字不雅,书信恐有数千年的历史,书信交往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虽日新月异,时代发展了,进入到信息化,网络化高科技时代了,交流、通讯形式大变了,那么记录回忆展现经历过出现过的一段历史,又有什么不可呢,何况,仅欣赏不同性格的各人来自不同地点各种写信人的字体、笔迹就不能不说也是一种乐趣,尤其在多少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