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此去经年,良辰好景何在
——王选《世间所有的路》的情感指向
天水日报
作者:深邃
新闻 时间:2024年09月05日 来源:天水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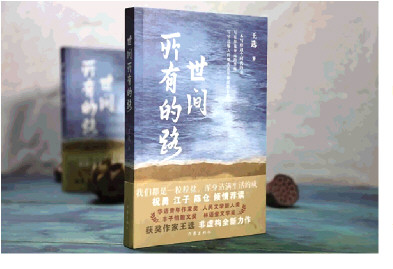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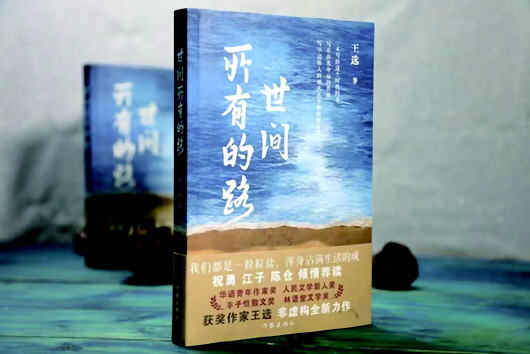
□ 陈晶晶
《世间所有的路》是王选2024年出版的长篇非虚构。全书分为归去、寄居、殊途、借过和萍踪五个部分,是作家半生经历的一次完整呈现。该书以作者的成长经历作为主干,呈现出了他人生旅程中遇到的纷繁人事,并以此构成了繁茂的枝叶,这使得他的写作绵密而厚实。回望旧时光,作者以“我”的感受联动“我们”的共同感受,写出了具有普遍性的群体运际。由“我”到“我们”,群声众和的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声音,也展现了一个时代的风貌。
溯回:一个人的自我怀旧
作者的半生经历是在城与乡之间“出走——归来——再离去”的不断循环。在社会的快速发展变迁中,回不去的故乡与融不进的城市成为作者的症结所在。因此在重返与离开的反复中,“麦村”“南城根”也成为王选反复记忆与书写的文学地理空间。
《最后一个村庄》《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中留存着作者关于“麦村”的年少记忆。《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中,作者书写了“麦村”的四季轮回与人事变迁。在《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和《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中,作者写自己在城中村的寄居、租房经历。《世间所有的路》更是在之前书写的基础上进行了延展,较之以往更为具象化,情感也更涌动而鲜艳。
作者出生于乡村,在贫瘠而荒凉的土地上生长,因此极力想要逃离,终于通过考大学离开乡村,但又被分配到了叫秦岭的小乡镇。在秦岭当老师,“我”无人说话,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对前途的渺茫以及对当下生活的无望让作者更显苦闷。正如作者写到自己“像一只蚂蚱,唱着七月悲伤的歌。”不甘于此,作者后来又去了城市,租房、借居,如浮萍般在城市生存。在莲亭、南城根寄居,居住环境阴冷潮湿,冬天没有供暖,生活艰难而苦涩。
作者四处搬迁,觉得一切都显得陌生而恍惚,甚至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错觉,寄居的生活让作者感到自己如一枚草芥,无处归依。可以说,作者的怀旧,是对自我心境的一次回望,是对过往的寻求以及对未来的确认。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对未来的考量使我们承担起对于我们怀旧故事的责任。”社会发展快速度而急促,作者从学生到成为记者、教师等不同身份,由麦村、天水、秦岭再到兰州不同地理空间,其间经历乡村的衰败、城中村的没落以及人世浮沉,一次回望便是一次记忆重组,一次自我找回,找到自己跌跌撞撞的来路,以此完成自我的重新确认与身份认同,从而也获得了面向未来的生存意义。
共情:一群人的命运铺陈
散文是有情的写作,情感始终是推动文本的密匙。王选以自我的经历作为主线,延展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流动,也打开了世间的豁口。在自我经历中,所遇的人和事成为王选书写的重点。他以共情心,展现了身处底层,日常烟火人间的琐事人情。
所谓共情,是一种从他人的参照体系中想象他人的感觉,理解和感受他人经历的能力,也就是把自己放在他人位置上的能力。从《南城根》《最后一个村庄》《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等作品中,王选始终以共情心来观照那些身处底层的平凡者,以“我”即是“他们”的写作情感,以群像的方式呈现了烟火人间的生活与运际。在《世间所有的路》中,王选依旧秉持群像的写法,在往事回溯中牵引出众多的人物,这些人物出现于作者人生经历的不同时期,有乡村、城中村以及城市中的人,也有小孩、中年人以及老人等不同年龄群体,这使得王选的书写广阔而深邃。
王选笔下的人物大都在生活的泥沼里艰难生存。他笔下有在城市租房陪读的母亲,有被兄弟算计一无所有疯了的虎头,也有一事无成的颓废者如老瓜。留守老人也是王选书写的一部分。那些已经嗅到死亡气息的老人大多是留守老人,要么坐在轮椅上发呆,要么经历着疾病的疼痛、子女兄弟间的纷争……在无奈中等待着黑暗的降临。王选以“我”的经历联结时空与人群,将书写变成了“我们”,以共情的视角,平视这些在生活中苦痛、挣扎、烦恼的众生,正如作者所说:“这世间那么多我们,多的是同我一样漂泊寄居无处安定的人。”生活波澜不惊,然细看,则多是褶皱,而褶皱里,则掩着喜怒哀乐、鸡毛蒜皮,掩着难以言说,抑或视而不见的东西。我们就是同一个人,何其相似。王选以此写出了人生的况味,写出了平凡的“我们”相似且共情的人生之路。即便如此,这些低入尘埃的人也努力寻求生活的甜。摊点、大排档等成为人们暂时的寄寓之所,在铁铲和锅底的摩擦声,吃喝者的划拳声、吆喝声、吹牛声以及汽车的喇叭声中,人们大口吃肉、喝酒,大声交谈,将生活的苦闷消化,从而获得前行的力量。
王选写出了这个世间艰难、困苦却也温情、温暖的复杂状态,将一个个血肉鲜活的小人物立于纸上,他不仅仅写他自己,更是写出了最普遍、最广泛、最平凡的个体如何生,如何死的日常。
透视:一个时代的悲与喜
一个人的声音和着一群人的声音,使得王选的作品具有了众声絮语的调性。无数个体的人生之路与命运悲欢绘就了一个时代的面貌,展现了时代的发展变迁。当现代化的进程席卷而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不仅有声势浩大、风云动荡的变革之音,也有日常生活的细微波动。正因此,王选致力于还原完整、流动的日常生活图景和人生本相,强调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对历史的捕捉,力图在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意义。
“最后一个”的书写是对现代化的有力反思,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阿来的“最后的蘑菇圈”“最后一位祭师”等等都展现了现代之变。在王选笔下,“变”是更加琐碎和细微的呈现。正如王选在《最后一个村庄》里写的:“日子就这么过着,不紧不慢,重叠着,循环着。像灶头的一碗水,用完了,舀满了。像墙头的月光,升起了,落下了。像阴山的雪,白了又黑了。像蹲在牙叉骨台晒暖暖的人,说了一句,忘了一句。然而日子变化着。在重叠和循环里,磨损了什么,也滋生了什么。灶头的碗,豁了牙。墙头的月光,挂在刺上,难以落下。阴山的雪,白着白着,就忘了黑了。晒暖暖的人,死了一个,又死了一个,日渐稀疏了。”
王选擅长写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职业甚至是场景的变化,从热闹喧嚣、温情脉脉到“再也不见”,这构成了他书写的情感冲突。初中的同学再也不见,南城根补鞋人再也不见,修自行车的人再也不见,卖蔬菜的人不来了,卖面鱼的也不来了,零工市场不见了,校门口摆摊的中年女人不见了……王选书写各种烟火日常的细碎、热闹与热情,也写它们的落寞、消失甚至是消亡。王选将书写敏锐聚焦于市井烟火、饮食日常,以小入微,切开了时代的另一面向。
城市作为现代化的焦点,在发展的浪潮里也会带来人心动荡与面目全非。在王选笔下,城市中以前熟悉的店铺都不在了,熟悉的藉滨市场被拆掉用来开发楼盘,改建与规划让原本的城市生活消失,也让原本凝聚的情感消散。城市是文明的场所,城市不允许落后与脏乱,因此所有“不文明”都将被城市所淘汰,当大量的空间、场景、物件都消失不见的时候,它们背后所粘连的人际关系与情感纽带也将分崩离析,王选以此呈现了历史车轮滚滚而过,人的悲欢与愁苦,人的断裂与为继。
散文是最见本真的写作,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说,散文的背后站着一个人,这个站立的人是否健旺、深邃、阔大,将直接决定散文写作的基本品质。王选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主线,呈现与他相似的无数人的命运悲欢,呈现一个时代发展的尴尬与变迁。他的写作敏锐而锋利,悲悯而温情。因此,《世间所有的路》献给每一位平凡者,致敬每一位用力生活的人,是一部从小处着笔,却写出大情怀的作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