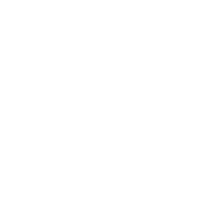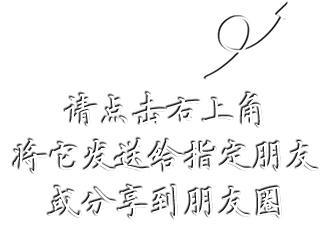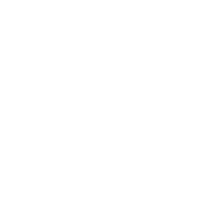父亲的剪刀
天水晚报
2023年11月20日
父亲年轻时是裁缝。那时他的梦想,是早日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剪刀。
初中毕业后,父亲开始跟随祖父学做衣服。刚开始,祖父只让父亲站在旁边看,不时教他一些缝纫的基本知识。半年后,祖父才让父亲上缝纫机练基本功,比如裤子拼缝、上袖子、上领子和上腰头。练基本功十分耗时,祖父练的是父亲的耐心。半年后,祖父见父亲基本功练扎实了,也不再毛毛躁躁,这才开始教他裁剪。至此,父亲终于有机会接触剪刀,并慢慢继承了祖父的裁缝手艺。
祖父五十多岁时因病去世,他用过的缝纫机、尺子和剪刀全都留给了父亲。父亲是家中长子,自感有责任担起家庭的重担,即使后来分家后,也总是强加给自己太多的责任。自我出生起,就很少看到父亲笑。有时候,我觉得父亲就像他手中的那把剪刀一样冰冷。
那把剪刀是用生铁打成的,比平常的剪刀要大上许多,刀柄裸露,通体黑黝,夏天沁凉,冬天刺骨。剪刀的两条手柄,一条弯成封闭的圆形,另一条则是单独一根铁柄。小时候,我试着用它去剪东西,却怎么也不会用。我们都不喜欢那把剪刀,父亲却视之为宝贝。他用那把剪刀裁衣剪布,一用就是一辈子。
早年,父亲也曾像祖父一样,以裁缝手艺为生。做裁缝需要经常熬夜,父亲有眼疾,一熬夜就会眼痛流泪。无法,父亲只得弃了裁缝手艺,转而务农,农闲时外出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但每年腊月间,父亲都会重拾那把剪刀,为我们每人做一套新棉衣过年。
有一年冬天,父亲去山里收猪鬃卖,直到腊月二十八那天才回到家。一进家门,父亲就拿出卖猪鬃的钱,叫母亲去扯几尺军绿色的棉布回来,他要为我们三兄弟每人做一件军大衣。白天,父亲要准备过年的吃喝用度,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时间给我们做衣服。老家腊月的夜晚,气温会降到零下二三度,父亲顾不上手上长满冻疮,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手握冰冷的剪刀,一边“咔嚓、咔嚓”连夜裁衣,一边不时擦拭因眼痛而流泪的双眼。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急切地问父亲军大衣做好没有,父亲总说快了快了。为了新年穿上军大衣,我哪管父亲晚上有没有睡觉,只是不停地催促他再快点。在经过两个通宵的加班后,父亲终于将三件军大衣都做好了。
大年三十的早上,我一睁开双眼,就看到放在床头的军大衣,马上迫不及待地穿上。在小伙伴羡慕的目光里,我穿着崭新的军大衣,在村子里跑来跑去,整个春节都欢欣鼓舞。那时,村里还没有哪个小孩子有军大衣穿。他们不仅羡慕我身上的军大衣,更羡慕我有一个会缝衣服的父亲。
小时候,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我躺在床上,耳朵里回响起“咔嚓、咔嚓”的声音时,便知道父亲又在裁剪衣服了,心中便会十分温暖、熨帖。懂事后,我逐渐明白,虽然父亲的那把剪刀是冰冷的,但经由它裁出的衣服却是那般暖和,正如父亲对我们永不停歇的爱一般。
有一天,那种“咔嚓、咔嚓”的声音却突然消逝了。二十年前的那个秋天,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按照村里的习俗,母亲将父亲的衣物和个人用品都烧毁或丢弃了,只留下了那把剪刀。如今,那把剪刀静静地躺在母亲床头的抽屉里,一如父亲正在另一个世界默默陪伴着她一般。
□ 百夫长
旧物华光